|
说到上海 人们第一时间想到的
往往是它的繁华 但是有关于它的历史 似乎并不是那么为人知晓
今天,在第二期《探寻上海之根》中 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由上海博物馆考古部主任黄翔 带领来到了 松江“上海之根”广富林遗址 黄翔主任一语中的地说 “源”代表着最早 而“根”则代表着不间断 广富林的人们从五六千年前 在此定居生活 这人间的烟火气便延绵不绝 从未消散 而事实上 只有把“源”和“根”的问题讲清楚 上海才能找到自己准确的历史坐标 
现场: 遗址下应该还有珍贵文物 和记者之前探访过的 考古现场或者遗址博物馆都不同 广富林遗址公园确实是一个“公园” 里面固然有遗址博物馆 有未发掘的遗址保护区 但也有酒店,有娱乐设施 所以这更像是一个沉浸式体验的空间 
“那栋白房子 过去就是一个村民的家里 我在里面住了300多天” 黄翔对记者说 广富林遗址迄今经过了4次考古发掘,分别是1999年、2001年、2003年,第四次发掘从2008年一直持续到2015年,长达7年时间。 黄翔告诉记者,广富林遗址考古发掘面积达到了7万平方米,“现在你所看到的遗址公园这些房子下面都经过了考古发掘。 
相比青浦崧泽遗址可能有一段时间无人居住(这只是学术界的一种推测),现在学术界普遍认为广富林遗址的五六千年的人类居住史一直没有断过。直到现在,这里还作为遗址公园供人学习、体验和娱乐。所以在黄翔看来,崧泽遗址被称为“上海之源”, 强调的是“最早”,而广富林被称为“上海之根”,强调的是“延绵不绝”。 黄翔把记者领到了一块稻田,颇为神秘地告诉记者,这下面应该还有珍贵的宝贝。这里是广富林遗址保护区的核心范围。所谓“遗址保护区”就是遗址内还未进行考古发掘的区域,广富林遗址公园里这样的区域大概还有4.5万平方米。 
发现: 这个做工精良的土台是做什么的? 黄翔从28岁一直待到35岁 几乎将最美好的青春都献给了广富林考古 考古发掘是一个耗时耗力耗心的工作 需要有极大的耐心 但是在黄翔看来 对那些未知惊喜的探寻 也正是考古这项工作最大的乐趣所在 
黄翔在广富林的7年之中 对于良渚文明晚期土台的发掘 让他印象最为深刻 也是他们团队一个重要的考古成果 该土台位于广富林遗址公园南区的中部,建于一处洼地之上,由人工堆筑草裹泥而成。黄翔说,开始他们还以为这是一处墓葬,但是后来随着发掘的深入,他们发现了五色土,就觉得情况没有那么简单。 
这处土台的建造不可谓不繁复。土质是草裹泥,土台外围采用草铺泥的结构进行加护,而在土台堆积中,黄翔他们还发现了两层由红烧土组成的斜坡状堆积。土台的东侧、北侧发现了一些与土台方向一致的长条形凹槽,部分凹槽中发现有竖立的篱笆痕迹,这一定也与土台的加固有关。黄翔告诉记者,由于沟槽及篱笆土台上部接近现代地表,受到严重破坏,所以目前并不能确定土台是干什么用的。但是依他的推测,这个土台可能是一个祭祀台。 
这个土台的考古发掘,对于认识良渚文明晚期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分工和社会等级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当然对于了解之后广富林文化的诞生和演变也有着参考价值。
影响: 让考古年代学精确到了百年 黄翔反复对记者强调 遗址和文化是两个概念 一个遗址上可能有多种文化 就拿广富林遗址来说 这里有崧泽文化、良渚文明 当然也有广富林文化 
长江下游地区的史前文化 有三个考古学文化 是以上海的考古发现而命名的 它们分别是崧泽文化、 广富林文化和马桥文化 黄翔告诉记者,开始广富林遗址出土的文物,大家也都认为是崧泽或者良渚时期的产物,但后来渐渐发现,有的文物和崧泽、良渚时期都不一样。比如陶鼎,崧泽文化的鼎是扁平而有脊的“铲形足”或者是“凿形足”,而到了良渚时期,陶鼎普遍是“翅型足” 或者是“梯形足”,广富林文化时期的陶鼎和之前就都不一样,其足是侧装的 “三角足”。 出土文物的这种差别多了,学者们就开始考虑这里是不是存在一种新的文化。最后他们确认,这里存在一个约4200年到4000年前的广富林文化。 
黄翔说 “广富林文化”的确认意义非常重大 ·其一,它填补了良渚文明(约5300年到4300年前)到马桥文化(约3900年到3200年前)中间的空白。 ·其二,它让考古学的年代学时间精度具体到了百年,这是考古学年代学的一次重要的飞跃。当然,这也让松江作为 “上海之根”变得更有据可循。五六千年前这里就有人生活,现在仍是,这是人类生生不息的最佳例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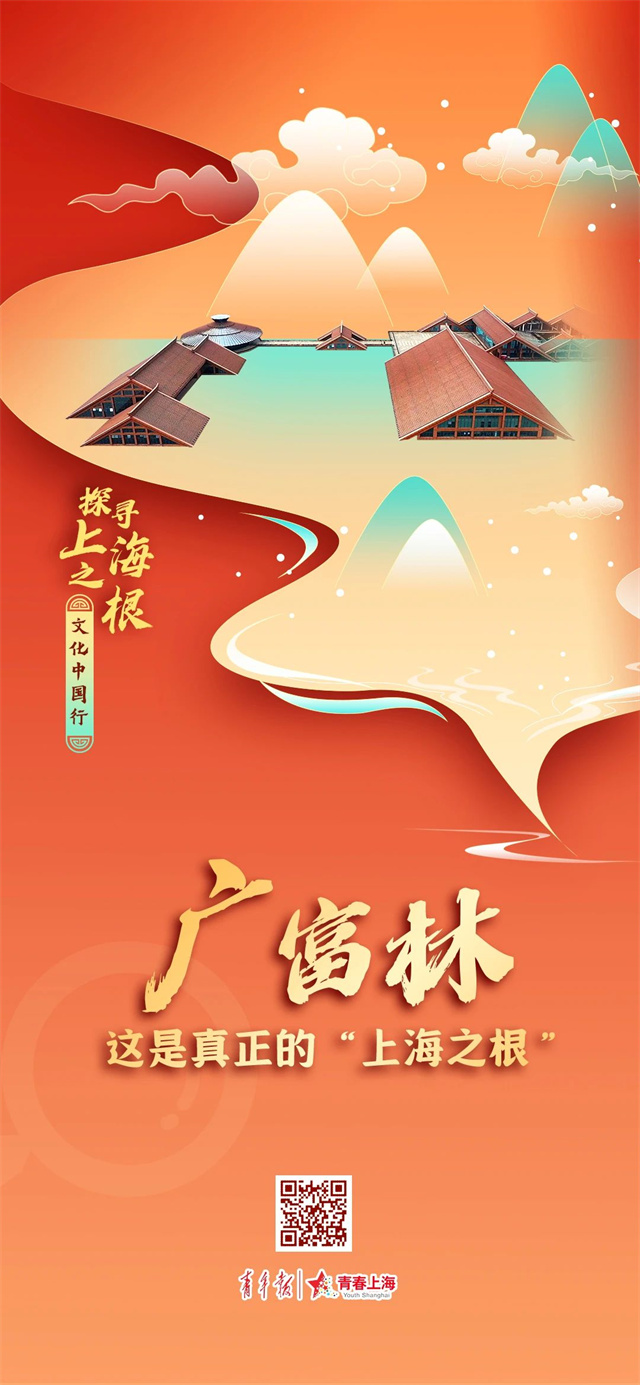
作者: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郦亮、常鑫 责任编辑:思瑞 校审:林桂人 终审:神小丢
|